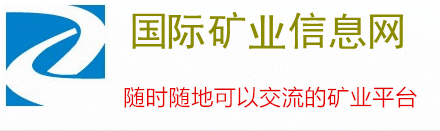从时间点来看,这是一次“非常重要”的会议。一方面,这是疫情期间少有的实体外交会议,是日本新政府主办的第一次重大外交会议,体现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延续性。另一方面,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与美国、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同时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。四国应对中国的战略需求显著上升。
美国仍然是“四国机制”的主要推动力。四国的第一次对话是在2004年,后来这一机制基本停止。2012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紧张和中国的内外政策变化,美国建立反华阵营的呼吁得到其他三国的更多呼应,“四国机制”于2017年重启。当然,这次美国国务卿取消其他访问保留东京之行,并非仅是为了对付中国,摸日本新政府对外政策的底,也应是一个重要目标。日本新首相延续了安倍关于“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”设想,似乎已得到了美国的认可。
日本的主张是四国在目前的最大公约数。日本的主张主要包括两点:一是,印太愿景是区域法治和自由航行。这是各方、包括四国以外的很多国家,都可以接受的概念。二是,日本意识到“美国一国独大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”,美国单边主导的安全机制逐渐失效,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多边安全机制,才有可能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。这意味着,日本要应对的,是一种体系性变化,并非必然是某个特定的国家。
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“制衡中国”是四国的共同目标,但由于地理位置、与中国关系以及对外政策传统的差异,四国在如何应对所谓“中国威胁”方面有显著差异。
美国的反华姿态最积极,不仅把“四国机制”定义为反对中国的战略集团,甚至还要吸收更多的国家参加,以组建出一个“亚洲版的北约”为目标。
与美国相比,其他三国则努力淡化“四国机制”中的反华色彩,更愿意强调其中的积极性和建设性。澳大利亚看待中国时,更多是出于价值观差异,而非具体的战略威胁和利益矛盾。日本的考虑比较复杂。一方面,日本要借助其他国家的帮助来敲打中国,改善在中国面前的博弈地位。另一方面,日本又不愿意与中国真正为敌。在四国中,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更近(跨过东海比翻越喜马拉雅山更加容易),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也更加复杂。此外,与中国为敌会降低日本在美国面前的国际地位,也会削弱其好不容易获得的战略独立性和自主权。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相比,印度参加“四国机制”的积极性更具有时效性,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紧张状态。印度试图借助一个更加紧密的、有组织的机制,来增大对中国的压力,迫使中国在相关问题上对印度让步。
虽然“四国集团”仍然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,但四国对话机制已成为事实上的四国磋商机制。四国虽然是在对中国打外交牌,但也已经认真地考虑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可能性,需要中国进行认真地思考和应对。这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。
一是,中国与美国的关系。霸权国家与地位邻近的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关系,是一个经典的议题,中国难以回避。但是,中国可以对博弈的烈度和方式选择施加自己的影响。二是,中国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。一个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地区秩序,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。中国应该大力支持这一概念。三是,中国与世界的关系,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的关系,需要更加科学的定位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,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,又汲取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有益经验。这既具有中国特色,又与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,当代中国是“既东又西、既中又外”。中国要强调自己在世界文明体系中“带有中国特色的共性”。只有这样,美国打着“价值观差异和文化差异”的旗号来建立反华同盟体系的努力,才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。中国才能破局。(作者张家栋: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/南亚研究中心主任)